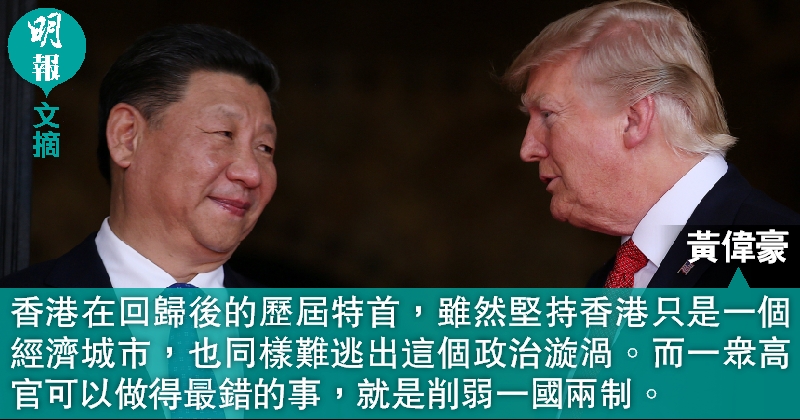中美貿易戰的本質,遠超於兩個大國的經濟較量,背後隱藏着複雜的政治矛盾。我們必須認清的兩個事實是,真正發生的並非貿易戰,而是用貿易作為手段的政治對抗,而且還是一場持久戰。山雨欲來,一切只是開始。
中美貿易戰爆發,雖然曾經使人感到突然和意外,其實原來是有劇本可依,並且已一早寫好,就是美國著名鷹派學者彼得.納瓦羅(Peter Navarro)的著作《致命中國》(Death by China;註)。今時今日,納瓦羅的身分並非是單純的學者,更是擁有實際權力的決策者——他是美國在總統白宮辦公室最新成立的國家貿易委員會(National Trade Council)的主持人。鯉躍龍門,自然聲價百倍,大家均相信他有能力把自己書中的理念付諸實行。
中美貿易戰有其深遠背景
由象牙塔跳入白宮,理論結合權力,自然洛陽紙貴,愈來愈多人一窩蜂地爭相閱讀《致命中國》,希望盡快了解他的思想和理念,以求明白這場貿易戰的基礎與脈絡。不讀猶自可,一讀便發現非同小可,發現冰封三尺並非一日之寒。這本書早在2011年已經出版,除了書籍外,更有依照這本書作為藍本拍攝而成的同名紀錄片。電影於2012年已在Netflix上架,近年更被上載至YouTube,使全球有興趣的人均可免費欣賞。平心而論,紀錄片的組織性及分析性均比書本強。在書中,作者只是如漫畫「尋死的兔子」(Bunny Suicides)般,把中國視為地球的癌症、人類的毒瘤,不斷列出在中國的威脅下,美國人各式各樣必死無疑的「死法」。
從時序可見,造成今次貿易戰的背後矛盾,早在特朗普於美國崛起及成為總統之前已形成。這反映這場貿易戰絕非全因特朗普一個人而引起,也並非暫時或偶然,而是有其深遠的背景和前因後果。
與其說貿易戰是由特朗普一個狂人一時衝動而引起,正確的解讀是,懂得把握時機的特朗普成功看透了形勢和時局,捕捉了在中國國力增強及美國經濟轉型下美國人的不安與排外情緒,進而順手採納了納瓦羅一早已準備好(ready-made)的針對中國的政策。
《致命中國》的電影副題是「美國如何輸掉它的工業根基」(How America Lost Its Manufacturing Base),正正和特朗普成功登上總統寶座的競選口號「讓美國再次偉大」(Make America Great Again)異曲同工、首尾呼應。在紀錄片中,它詳細列舉及說明了中國擁有用來對付美國、破壞公平貿易(fair trade)的四大「消滅職位的武器」(weapons of job destruction),分別是:破壞環境以牟取利潤(polluting for profit)、虐待工人(worker abuses)、匯率操控(currency manipulation),和偽造與盜版行為(counterfeiting and piracy)。在電影結尾,便提出必須要向中國宣戰,雖然是用上了「貿易改革」(trade reform)這個雅稱,而非「貿易戰」這樣露骨的強硬字眼。所以,貿易戰的計劃早已是個公開秘密,一切也只因納瓦羅未正式掌權而被外界忽略。
作為這場貿易戰的首席智囊和靈魂人物,納瓦羅一早已開宗明義,表明這場針對中國的「戰爭」的定位是遠超於經濟與貿易,這些只是達成目標的手段而已,政治與權力才是真正的定位。在電影中他不斷形容中國為世界上最大的共產及極權國家,他更把《致命中國》一書獻給中國人民,並在書中第一頁寫下以下句語:「這書是獻給我們的中國朋友,希望他們有朝一日可以活在自由當中,在這一日來臨前,他們可以平安。」(To all of our friends in China. May they one day live in freedom-and until that day, remain safe.)這顯示一切的最終目標也是要推翻中國的共產和專制政權,以解放中國人民,甚有冷戰味道。
中國國際形勢孤立嚴峻
從一個歷史發展的宏觀角度分析,中美兩國的競爭與對抗,才是蘇聯解體後的後冷戰時代的國際政治形勢和新趨勢。曾幾何時中美關係曾一度緊張,好記性的朋友應仍記得在2001年,小布殊當總統及江澤民執政的年代,便發生了中國戰鬥機和美國EP-3間諜機在空中相撞的事件,導致中國機師死亡,而美國間諜機在海南島被迫降及扣押。一切只因在幾個月後,在美國紐約發生了舉世矚目的9.11恐怖襲擊事件,美國外交策略才突然戲劇性地來了一個180度急轉彎,把中國由原來的競爭對手,定性為在全球反恐戰下的策略伙伴。在同一年,中國亦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(WTO)。在這大好形勢下,中國開展了長達10多年的黃金發展期,最後更放棄了鄧小平的韜光養晦教訓,走向大國崛起。
可是,民主和極權始終是兩個難於共存的制度。隨着反恐戰結束,中美的緊張關係又再重回「正軌」,而民粹主義的特朗普及鼓吹民族主義的習近平,分別在兩國上台執政,也大大加速這趨勢的發展。雖然俄羅斯也是美國的威脅,但她「假假地」也是一個可一人一票選總統的「混合體制」(hybrid regime),算是比中國進步。俄羅斯的野心,也有以德國為首的西歐幫手制衡。隨着特朗普和普京的關係親密得非比尋常、美國和北韓的關係全面解凍,中國的國際形勢便更顯孤立和嚴峻,只餘下一班用錢買回來、主要來自非洲的「忠實」盟友。
香港難逃中美政治漩渦
雖然經濟已全球化,但政治仍然受制於國內形勢(all politics is local)。因對抗中國的策略完全符合了特朗普支持者的口味,貿易戰只會持續和不斷升級,更是他連任的本錢。在這新形勢下,即使你討厭或不理政治,政治最終也會自己找上門,並使你付出沉重代價。在這道理下,香港在回歸後的歷屆特首,雖然堅持香港只是一個經濟城市,也同樣難逃出這個政治漩渦。而一眾高官可以做得最錯的事,就是削弱一國兩制,使香港焉能獨善其身之餘,也難再擔任中國的世界窗口的緩衝角色,累己累人。
註:Navarro, Peter, & Greg Autry.(2011). Death by China: Confronting the Dragon-A Global Call to Action. NJ: Pearson Education.